多发性骨髓瘤的髓外病变——争议与未来方向(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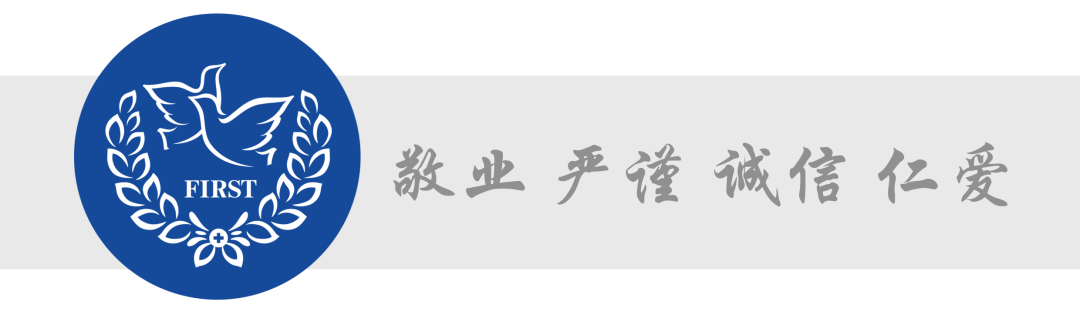

摘要
目前还没有针对EM特异性治疗的前瞻性研究,故很难推荐特异性治疗方案。EM患者通常具有高危特征,如高LDH水平、高危细胞遗传学或高危基因表达谱。因此专家建议EM需按照高危MM治疗。对于需要使用大剂量化疗的EM患者,建议采取三联诱导治疗,后行单次或双次外周血干细胞移植(PBSCT),三联巩固治疗,和至少包括来那度胺在内的维持治疗。同时可应用放疗来改善局部病灶控制及镇痛。
Gagelmann等(2018)的研究显示MM患者接受单次或双次移植,其治疗效果相近(81.6% vs 84.7%)。对于EM-B型,其疗效与MM组类似,且单双次移植疗效相近(82.6% vs 80.3%)。对于EM-S型,单双次移植的疗效差异不大(76.9% vs 77%),但要低于MM组。
异基因干细胞移植对MM治疗疗效尚未明确,且在标准化治疗中并不推荐。但对于预后不良的高危患者可能有一定获益,且不良预后可能造成的影响或许超出移植相关的风险,因此在初始治疗或首次复发时可考虑采取。然而移植对EM疗效尚存疑。更何况,一些文献认为移植后EM的发生率更高。
先前有报道称沙利度胺对EM疗效差。IMWG共识声明提出沙利度胺不能消除高危因素带来的不良影响。Blade等(2011)也发现与其他MM患者相比,沙利度胺对EM治疗无效。
相比之下,硼替佐米对EM治疗似乎更为有效。硼替佐米针对高危MM的t(4;14)或del(17p)有作用,但当存在t(4;14)联合del(17p)时可能治疗无效。来那度胺作用目前尚有争议,专家小组不建议将其用于高危MM的维持治疗,除非将其与蛋白酶体抑制剂联合使用。卡非佐米联合来那度胺和地塞米松似乎对高危患者有效,是此类患者的首选治疗方案。但目前关于卡非佐米的疗效研究成果较少,最近病例报道有一例在卡非佐米联合地塞米松治疗后表现为长期完全缓解状态。Short等(2011)研究表明泊马度胺治疗EM后有30%有效率,同时对髓外病灶有效。此外,泊马度胺对del(17p)患者疗效理想,但无法消除所有高危细胞遗传学改变带来的不利影响。Sirius试验证实达拉单抗对EM部分有效。捷克某项针对单一达拉单抗药物治疗后的患者真实生存研究报告也得出类似结果。
对于CNS-MM治疗,已试验多种方案,例如新药(蛋白酶体抑制剂和免疫调节剂),鞘内化疗(IT),以及由阿糖胞苷、甲氨蝶呤和氢化可的松等组成的方案。异基因和自体干细胞移植、颅脑辐射照光也均有运用。无论选择何种治疗方式,所有患者都会在CNS-MM诊断后的短时间内死亡。Gozzetti等使用新疗法(硼替佐米、沙利度胺、来那度胺),旧药物(长春新碱、甲氟烷、泼尼松),干细胞移植,鞘内化疗,放射疗法,外科手术治疗CNS-MM,但结果显示这部分患者的中位OS为6个月。
新型疗法例如单克隆抗体或CAR-T治疗,有可能提高生存率并可能克服EM患者的不良预后。不过治疗后真实转归情况仍需要长期的随访评估。目前即使是骨髓瘤专家也无法就EM治疗指南达成共识。
最近有研究者对EM危险因素展开研究。Varga等(2015)对来自于8个不同临床试验的117 例MM展开研究,所有患者接受硼替佐米联合或不联合来那度胺治疗,无证据显示该治疗方案会诱导EM发生。通过单变量分析显示既往MGUS病史和低血红蛋白(<120g/L)者发生EM-S的时间趋势更短(分别为p=0.06,p=0.05)。多变量分析校正后发现只有MGUS病史与EM-S的发生时间有轻微相关性(校正p=0.06),然而该分析存在一定局限性。对于EM-B,多变量分析显示只有钙水平升高(≥2.5mmol/L)提示预后不良。ISS III期患者的EM-S发生风险增加,但这种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有可能是因为病例中ISS III期的发病率较低(占9%)。
另一方面,Weinstock等(2015)收录的55例EM患者在诊断MM和EM时均表现为轻度贫血和轻度LDH升高,这表明血红蛋白和LDH水平都不能用来可靠地预测EM在MM患者中的发生。
Mangiacavalli等(2017)研究指出对于伴有溶骨性病变和高钙血症的患者发生EM的风险明显更高。骨髓中浆细胞浸润比例升高也使得EM发生风险增高。与没有危险因素的患者相比,一或两个危险因素都可导致EM风险升高。所有第一代新型药物(硼替佐米,沙利度胺,来那度胺)所致EM发生风险相当。多变量分析证实MM治疗史与EM发生密切相关,当存在一或两个治疗相关的危险因素时,EM的发生风险显著升高。遗憾的是,没有基础特征可以用来预测EM的发生。单因素分析提示溶骨性病变、高钙血症及浆细胞骨髓浸润与EM发生有显著关联,但未在多因素分析中得以证实。
只有少部分研究仔细探讨了髓外病变处的浆细胞形态及遗传学异常。一些报道称这些细胞具有不成熟或浆母细胞形态。另有研究则表明骨髓与髓外病变的浆细胞在细胞遗传学异常方面不存在差异。
我们评估EM及前期MM诊断时患者浆细胞染色体畸变情况(来自骨髓或髓外组织)。使用iFISH(间期荧光原位杂交)技术,检测常见的染色体异常(del(17)(p13),del(13)(q14),14q32断裂,t(4;14)(p16;q32),t(14;16)(q32;q23),超二倍体状态等)。总体而言,t(4;14)在髓外肿瘤的浆细胞中常见,超二倍体则在EM的骨髓象浆细胞中多见。EM患者在所有研究中的骨髓浆细胞染色体畸变频率均高于先前MM诊断时。
Deng等研究表明原发性EM比MM患者更常见p53缺失。Billecke等分析了EM-S、EM-B型髓外组织浆细胞的细胞遗传畸变,结果显示del(p53)的发生率相近(32% vs 27%),t(4;14)的发生频率则在EM-S型更高(37% vs 18%)。 尽管该研究分析的病例数较少(总共36位患者),但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研究,因为它直接对比肿瘤浆细胞的细胞遗传学。Gozzetti等(2012)对CNS-MM的细胞遗传学检测分析表明del(13q)是最常见的染色体异常,但FISH分析不能评估预后。
遗憾的是,目前很少有关于EM潜在的分子机制研究。大部分研究报道只是一些样本数据,故EM精确的分子机制仍不得而知。
EM浆细胞可在骨髓外存活,似乎EM改变了对骨髓微环境的强依赖性。CXCR4的信号通路与骨髓瘤细胞归巢、扩增有关,因此该信号通路在EM有可能被消除。Roccaro等(2015)研究表明CXCR4更高的表达可能导致EM发生。骨髓瘤细胞存在于骨髓基质旁,表达VLA-4,CD56和CD44,可与内皮上的受体(例如VCAM-1)相互作用。此外还有几种趋化因子,例如CCR1,CCR2和CXCR4,它们对于骨髓瘤细胞迁移和粘附有重要作用。因此需涉及几种机制方能使浆细胞实现髓外转移,例如粘附分子的表达降低,趋化因子受体的下调,血管生成的变化(主要涉及VEGF,MMP-9和其他因素)以及典型或非典型NF-κB途径突变。治疗相关EM的发生与CXCL12 (SDF-1a)/CXCR4结合体有关,其促使浆细胞与周围的骨髓基质相互作用。有发现在先前使用沙利度胺治疗的患者中存在这种配对体的表达下调。
EM最可能与骨髓瘤细胞的生物学行为改变相关。Sheth等(2009)表明TP53, CD56和Ki-67的表达与EM发生有关。p53可能积聚在EM肿瘤的细胞核中,p53的失活使得MM疾病侵袭性更强,化疗耐药以及OS变短。CD56是神经细胞粘附分子,在细胞粘附和迁移中起重要作用。已有报道显示EM中存在Ki-67表达增加,CD56下调,p53缺失。此外另一研究也证实EM患者CD56的下调,但相反的是,与MM患者相比,EM的CD56和cyclinD1(CCND1)出现过表达情况。
最近一些研究着眼于非编码RNA分子及二代测序的探究。Haart等(2016)对MM和EM患者的BM活检样本(经福尔马林固定和脱钙处理)进行测序,结果发现EM患者具有高频率的RAS突变,大部分为诊断时检测所得,然而TP53突变频率在EM中更低,且多在疾病复发时出现。
虽然90%的人类基因组有转录活性,但实际上只有约1.5%表达蛋白质。不翻译成蛋白质的RNA成为非编码RNA分子,主要有两类:短非编码RNA(短于200nt)和长非编码RNA(长于200nt)。
MicroRNA(miRNA)是短非编码RNA,参与细胞增殖、分化、凋亡及肿瘤发生。更有多次证实miRNA参与到MM的发病机制。此外,这些分子可以在各种体液中找到(外周血、尿液、母乳、唾液等),由于它们与各种蛋白质结合或存在于外泌体内,相当稳定,可以用作疾病标记。本文作者及其他研究者已经指出将这些循环分子作为MM诊断标记,并且我们研究组显示循环型miRNA,特别是miR-130a可被用作EM的循环标记。循环型miR-130a可将EM与HD区分开来,特异性为90.0%,敏感性为77.1%。EM患者循环型miR-130a与骨髓浆细胞浸润有关。此外,EM患者髓外肿瘤浆细胞内miR-130a表达量较骨髓浆细胞有增加(p<0.0001)。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低水平的miR-130a与EM有关。然而该循环分子真实作用仍需要进一步大数据验证。
长非编码RNA分子(lncRNA)为大于200核苷酸的RNA转录物,不表达蛋白。它参与包括肿瘤发生等多个过程。部分研究证实了多种长非编码RNA在MM、MGUS和健康个体间存在表达差异。我们的研究表明UCA1在MM进展中起作用。Ronchetti等(2016)研究表明MALAT1在 MGUS转变为MM、PCL过程中起作用。Handa等(2017)研究显示MALAT1在MM和MGUS存在表达失调,EM患者髓内浆细胞MALAT1表达量高于MM患者。与髓内浆细胞相比,EM髓外肿瘤浆细胞的MALAT1的表达上调了几千倍。MALAT1位于11号染色体,邻近cyclinD1,并在IgH增强子作用下表达上调。有趣的是,对有11号染色体三倍体及t(11;14)MM者,MALAT1不出现上调,也与cyclinD1表达无关。此外,用蛋白酶体抑制剂和阿霉素治疗可增加MALAT1的体外表达。尽管目前关于非编码RNA参与EM发病机制的研究很少,但这些分子可能对理解这一发病过程中很有价值。
尽管蛋白酶体抑制剂和免疫调节药物显著提高MM患者的生存期,但EM仍是难题。新影像学技术虽得以运用,EM实际发生率仍有可能被低估。EM的发生率在年轻群体中更高(可能是由于MM更具侵袭性),并且随着数次病情复发进展EM发生率不断增加。由于EM患者的骨髓瘤细胞不依赖于骨髓,且有不良细胞遗传学异常趋势,目前新药对EM治疗效果有限。EM患者比无髓外累及者预后差。此外,EM累及软组织者相较于累及骨组织者具有更差的治疗反应及预后。最新的治疗方法,包括结合针对不同途径的新药物,可能会克服髓外播散的不良影响。
目前迫切需要统一对EM的定义,并纳入软组织和骨相关的各类EM。此外,需明确诊断方法,特别是能够在新诊断和(或)复发的MM患者中检测到EM的敏感的影像学技术。新的指南应该包括EM髓外肿瘤大小的随访以及肿块的缩小应该是EM患者治疗反应的一部分。
潜在分子机制的更多证据对于更好地理解这种疾病是必要的。对于非编码RNA的认知提升可能帮助至少阐明一些导致EM的病理过程。目前还需要更大规模的研究和更多的数据来证明它们是EM的病因还是结果。不管结果如何,这些分子可能对诊断和潜在的治疗都至关重要。
尽管MM的临床管理有很大改善,但EM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相关阅读
- 09-13 第八期“浙大市一.临床大讲堂”预告
- 05-24 2021年第三届湖畔眼底病高峰论坛暨浙江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玻璃体视网膜疾病诊疗进展》圆满举办
- 10-29 COVID-19流行期间重症监护中的床旁肺部超声
- 10-29 肝硬化患者的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和腹膜外感染(上)
- 10-20 妊高症回顾(上)
- 10-20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与心血管疾病相关发病率和死亡率的系统评价分析
- 10-07 急性心梗后超声可发现的机械性并发症
- 10-07 做了一回赵半仙--高血压心脏病
- 10-07 综合生命支持降低暴发性心肌炎死亡率的多中心研究(上)
- 10-07 经鼻雾化吸入(上)
